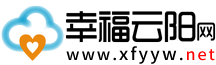世界湿地日③丨索郎夺尔基:拖着打狗棒守护湿地十余年
四川在线记者 王代强
2月2日,正月初二,世界湿地日。
阿坝州若尔盖县城的家里,索郎夺尔基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工作微信群,提醒保护区巡护员别忘了当天的草原防火巡查。
作为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科科长,虽然这天不是他值班,但索郎夺尔基心中始终放不下,隔几分钟就刷刷微信群,问问巡护员有没有发现破坏湿地的行为,随时准备到现场去解决问题。
保护区管理局2007年成立当年,索朗夺尔基就参与到若尔盖湿地保护研究工作中。十余年来,他参与见证了若尔盖湿地的变化,自己也从一名门外汉成长为湿地保护专家。
“干一行爱一行。”他也一度转到更加舒适安逸的单位工作,但后来又主动申请调回保护区管理局。索郎夺尔基说,是湿地给了他新的价值追求、生活意义。
从小学教师到保护区科长,追随专家成为专家
今年42岁的索郎夺尔基,是土生土长的若尔盖人。1998年,18岁的他从马尔康民族师范学校中专毕业,被分配到若尔盖县唐克乡(现唐克镇)中心校当语文老师,一干就是8年多。
直到2007年,保护区管理局成立,急需工作人员。考虑到父母年事已高,自己还未结婚,他便到了保护区管理局上班。领导告诉他,冬天没啥事做,夏天就去给科研人员带路。
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高寒泥炭沼泽湿地生态系统和黑颈鹤等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管理局就是为相关工作提供服务。
当年3月,他接待了第一批从成都某科研机构来的师生,到保护区研究高原林蛙的行动轨迹。“我会汉语和藏语,给他们带路和当翻译。”索郎夺尔基说,当时他们一共抓了12只,分别安装了跟踪器,记录察看它们24小时内走了多远。
对于这样的工作,索郎夺尔基感到非常新鲜。外来的科研团队越来越多,他就跟着团队的专家老师学习,加了专家的电话微信。如何识鸟、如何修复湿地、如何科学放牧,这些问题,他不懂就问,然后在下乡宣传湿地保护政策时,将这些知识讲给当地牧民听。
“我们在花湖安了监控,我每天上班把监控打开。”索郎夺尔基说,2020年3月,他突然看见一只鸟和以前看到的都不一样,立即截了图发给鸟类专家看。“专家说是东方白鹳,紧跟着新闻也出了,但是很多人不相信。”索郎夺尔基第二天又盯着监控发现了这只鸟,立刻开车去现场拍了清晰照片再次发给专家。
最后大家确认,这确实是保护区以前没出现过的新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在四川,这个鸟也是第一次被拍到野外的图片和视频。”他自豪地说。
刚到保护区时,这个藏族汉子连黑颈鹤是啥都不知道。现在,他已能独立识别出多种水鸟,对保护区里的黑颈鹤监测点位、每年来了多少只、迁徙路线等信息,了然于胸。在他的努力下,保护区开始开展自然教育,教年轻人识花认鸟。
越野车的后备厢常备打狗棒,制止打鱼被恶语威胁
不管是不是工作日,索郎夺尔基都喜欢驾驶一辆越野车,在保护区周边转悠。十多年来,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另一项任务——湿地巡护。
其实,他刚到保护区时没有车,只能借老百姓的马去巡护,保护区里到处都是沼泽,就算老马识途,也常常举步维艰。
后来,“坐骑”变成了摩托车,再后来变成了越野车,但险情依然存在。2009年,他陪北京林业大学一个学生进保护区做植被调查。学生不慎掉进沼泽,身子慢慢往下滑。索郎夺尔基赶紧从车的后备厢取出一条打狗棒,将学生慢慢拉了上来,“衣服、裤子、相机、GPS全报废哦。”
开车巡护还要带打狗棒?“草原上狗多,有老百姓养的也有流浪狗,凶得很。以前下乡骑摩托,前面的骑车,后面的拿棍子,时间长了,成了习惯。”他笑着说。
巡护的一大任务,是宣传湿地保护政策,制止破坏生态、违规盗猎等行为。“保护草场湿地,就是保护自己。”索郎夺尔基常常将这句话挂在嘴边。
曾经,他在巡护中发现违规打鱼的达扎寺向东村村民莫郎。索郎夺尔基不急着上前制止,而是买来猪肉、蔬菜,送给他,给他交朋友,然后耐心讲保护政策。后来,莫郎成了保护区聘用的生态管护员,从打鱼者变成了监督者。
有时也会遇到“硬茬儿”。一次,索郎夺尔基将一群违规打鱼者抓了个现行,没想到对方火气很大,认为被断了财路,威胁要报复他。他马上联系林业和公安部门,才消除了这场危机。
十多年来,面对威胁,索郎多尔基从未退缩。“现在保护区内违规打鱼的现象基本没有了。”
湿地生态改善肉眼可见,需要培养本地专业人才
近年来,随着一系列湿地生态修复工程在保护区落地实施,保护区生态环境的改善肉眼可见。
“相比十多年前,花湖的水位长高了30厘米,面积扩大了两倍多,过冬黑颈鹤数量从400多只增加到1000多只。”索郎夺尔基欣慰地说。
不过,他同时注意到一个现象。近些年,保护区降雨量逐渐增多了,虽然对湿地保护有好处,但背后是不是全球变暖的因素导致,这值得深思。
他的另一个担忧是,保护区内不少交通通道、防火通道缺乏更新维修,出现了一些危险路段。“有些地方桥断了,但小孩上学、老人看病都要从这里经过,现在是简单搭块木板就过人,太危险了。”
还有草原防火。尤其是枯水期,大量牧草干枯,火灾隐患大,如果防火通道不能用,消防车不能及时开到目的地,容易引发更大危害。
此外,他也为保护区周边老百姓的生活担忧。我省正在创建若尔盖国家公园,范围涉及保护区,如何科学平衡湿地等生态保护与老百姓放牧生产之间的关系,确保牧民收入不降低,不返贫,需要相关配套措施及时跟上。
对于保护区科研工作,索郎夺尔基最关心人才队伍支撑。“基层工作条件比不了大城市,如果没有优越的待遇支持,很难吸引专业又稳定的科研人才。”他建议,加大对本地人才的培养支持力度。
其实,在2016年,索郎夺尔基就有了一个看起来“更好的机会”——去县里环境整治办当一把手,但他只干了一年多,就闹着要回去。
“我不喜欢坐办公室,我喜欢呆在草原上。”索郎夺尔基一路“告状”告到省林草局,闹了半天,又回保护区了。用他的话说,就是“干一行爱一行”。
索郎夺尔基告诉记者,他的名字在藏语中是“幸福、金刚”的意思,现在的他很幸福。
图片均为工作中的索郎夺尔基(受访者供图)
标签: 湿地
相关文章
新闻快讯
X 关闭
资讯
X 关闭
新闻快讯
- 世界慢阻肺日 | 警惕“沉默的杀手”!它排四川单病种死因第二,“知名度”却很低!
- 四川昨日新增省内感染者208例、省外来(返)川感染者95例
- 四川新增三家检验检测类重点实验室0世界球精选
- 以三星堆神树为灵感 她耗时两年做出银花丝重器
- 外地的“熟面孔” 带着项目参加科博会3全球观热点
- 【天天新要闻】市州观察丨一杯“好茶”这样炼成,通江的绿茶获评“四川最具影响力茶叶单品”
- 科博会丨第十届科博会“新”在哪?2聚看点
- 环球观察:协议投资总额122亿元,攀枝花集中推进5个重大招商引资项目
- 四川评定首批10家省级农业国贸基地
- 四川出台实施意见,加强质量基础科技创新3世界即时
- 探访全省公立医院唯一手腕科:医生在鼠尾血管上练习缝合技术
- “凉山3名民辅警抓捕毒贩途中牺牲”追踪:车辆坠入300多米高山崖,涉毒嫌疑人当晚被抓获0环球精选
- 天天快资讯丨聚焦科技创新、成果落地,四川省动力电池创新联合体在宜宾三江新区揭牌
- 【世界热闻】四川首部线下消防主题剧本杀作品发布
- 组图|川西群峰“补妆”后更加雄伟
- 当前观察:冬日暖阳下青龙湖美景醉游人
- 最新快讯!广安市昨日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7例,涉及3地
- 四川昨日新增省内感染者190例、外省来(返)川感染者119例
- 遭遇夏季高温干旱 为何多地大豆创下高产?
-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数字化赋能基地投用0快报
- 巴中市巴州区解除临时社会面管控,主城区已连续3日无社会面新增
- 【独家焦点】市州观察|攀枝花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51.69万亩
- 四川出台新规:采砂河道修复将作为下年度采砂许可的重要依据
- 市民可在健康成都官微查询不同场所的核酸时限要求2世界微动态
- 今头条!祝贺!六家银行分获省金融大数据分析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团体奖
- 拼搏的时辰|辰时,这里有群赶早的税务人
- 焦点速看:近期,成都局部疫情主要关联大型农贸市场、茶楼、酒吧和货运场站
- 【天天报资讯】文体旅融合发展,“旅游马拉松”在古蔺县举办
- 四川启动首批高层次社工专业人才培养工作
- 从事竹编60余载 他成为国家级“中国工艺美术大师”3当前视点
- 成都市举办多场青少年冰雪活动0环球观焦点
- 11月13日,巴中市新增本土3+8,活动轨迹公布1全球视讯
- 视觉四川 | “观天神器”现稻城 子午工程二期圆环阵太阳射电成像望远镜完成系统集成
- 华西天府医院暂停发热门诊接诊工作1天天短讯
- 联合国糖尿病日丨它是四川上涨最迅速的单病种死因 专家这样建议
- 环球微动态丨成都疾控紧急提示:对照自查,尽快报备
- 世界热点!全明星周末活动落下帷幕 前NBA总冠军球员巴特尔跨界PK羽毛球众明星
- 重点聚焦!30名选手竞逐四川省殡葬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决赛
- 9片“莲叶”横跨锦江 成都将添一座“莲桥”
- 四川-重庆象棋名手赛个人组比赛落幕2热讯
- 四川举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野下的藏羌彝走廊研究”学术研讨会
- C视频︱秋天色彩下的缤纷生活
- 【环球速看料】直击“火焰蓝” 川观拍客镜头下的“紧急救援”
- 市州观察丨护航重大项目落地落实,资阳建立“6543”工作机制
- 世界快报:当前全球规模最大的太阳射电成像望远镜设备主体在川完工
- 郎利影任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副厅长 李庆峰任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
- 速看:四川昨日新增省内感染者75例,外省来(返)川感染者101例
- 阿坝州第五届美食烹饪技能大赛在小金县开幕4环球热闻
- 信息:第十届四川文学奖、第八届四川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作品奖颁奖
- 最资讯丨第35届金鸡奖在厦门颁出 峨影出品《漫长的告白》获两项大奖
- 观热点:纳溪区委书记谭荣兵:打造国内知名文旅融合发展生态旅游目的地|专访新天府旅游名县书记
- 理县米亚罗红叶温泉冰雪季将于11月20日开启1全球今亮点
- 世界快看点丨2022“彩虹杯”天府·宝岛工业设计大赛川茶品牌创新设计对接会走进乐山
- 时光映画馆|糖酒会35年:洋溢着欢笑的“舌尖盛宴”
- 铁路网加速织密,助力四川跨入全国高铁“第一梯队”0全球速读
- “迎汤尤杯” 2022西部羽毛球文化节开幕4环球快看
- 天天视点!“快递”发送!在川央企护航天舟五号货运飞船成功发射
- 四川警方破获特大假冒商标案:涉案5000多万,16人落网4天天速读
- 焦点要闻:计划投资100亿元!四川旅投集团与峨眉山市签约建设太阳谷国际旅游康养度假区
- 世界信息:2022年第四届大凉山国际戏剧节开幕,20多部中外剧目轮番上演
- 天天短讯!泸州警方破获一起危害野生动物案件,夫妻开服装店掩护非法收购
- 当前视点!四川体育2022年好新闻评选活动开始
- 当前最新:四川省高素质退役军人村支书培育试点工作启动
- 环球新动态:四川省网络举报一体化机制建设培训班在宜宾基地举办
- C视频|空军节!军地携手开展国防教育 共同守护祖国万里长空
- 为乡村振兴再助力,中国延安干部学院领衔为越西引来农业专家团
- 农民工朱祥洪的冠军之喜:感谢大赛让我有机会申报四川省技术能手
- 拼搏的时辰丨卯时:直击大型“翻车现场” 两小时卸煤超千吨0环球实时
- 省委宣讲团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宣讲2快播
- 好消息!国产化首件1000MW超超临界机组FB2转子研制成功4世界热文